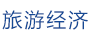馬可·波羅寫道:馬幫就是在這樣的險阻之地行進的

在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,南絲路上走過的有名人物當然不止司馬相如這么一位。1271年,一位少年跟著自己的父親和叔父,從威尼斯出發,沿著“絲綢之路”,前往東方,尋找當時一位對他們來說頗具神秘色彩的統治者——忽必烈。這位少年,就是后來很有名也同時很有爭議的著名商人、探險家和旅行家馬可·波羅。
馬可·波羅在中國生活了十七年,他借護送闊闊真公主遠嫁阿魯渾國王回到歐洲。
離開故土25年以后,三位波羅先生回到了家鄉威尼斯。43歲那年,馬可·波羅參加了與熱那亞人的戰爭,并不幸被俘。被俘期間,他向魯斯帝謙口述了自己在中國的這段經歷,也就是后來的《馬可·波羅游記》(又譯為《馬可·波羅紀行》《東方見聞錄》)。
盡管馬可·波羅是不是到過中國在學術界爭議很大,但他在書里,的確詳細記載了一些符合當時中國情況的內容。這本書里面,馬可·波羅也詳細記錄了他在中國西南包括南方絲綢之路的一些見聞。入朝為官經南絲路由蜀入滇
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院長王川介紹說,馬可·波羅和父親、叔父到達中國時,正值元朝初年的鼎盛時期。有學者認為,年輕的馬可·波羅受到了忽必烈的賞識,得以入朝為官,并且出于職務便利游歷了中國不少地區,到四川、云南等地的游歷便是這期間的職務行為。
在勞倫斯·貝爾格林所著的《馬可·波羅》一書里,馬可·波羅被忽必烈派去西南收稅,也有學者認為,馬可·波羅當時是個管理鹽務的小官。在游記里,馬可·波羅回憶自己從北方達到“蠻子省”,然后一路向西南,經“成都府”“西藏”“建都省”到達“哈喇章省”和“匝兒丹丹省”和“永昌城”,并到達了東南亞的緬甸、越南一帶。回去的路線則是經敘州到成都,再回中原。
巴蜀文化研究專家袁庭棟介紹,以馮承鈞先生的中文譯本為例,蠻子省指的應該是今天的漢中平原和川北一帶,西藏并非今日的西藏自治區,而是今天的甘孜地區,建都就是建昌,即西昌一帶,而哈喇章省和永昌城則是今日的云南,具體點說,哈喇章地區在今日麗江、大理一帶。敘州則是今日的宜賓地區。所以我們可以大膽推測,馬可·波羅入西南和出西南所走的兩條路線,分別是南絲路的牦牛道和五尺道。絲綢鹽金馬可·波羅眼里的西南
在馬可·波羅眼里,西南地區是一片另有風情的地域,這種風情與歐洲,與北方的蒙古貴族完全不同。例如成都府周圍的高山是不少大江大河的發源地,河流兩岸有要塞,河中船舶載著大批商品川流不息。成都府的水來自周圍的河流,河上的一座大橋上面有鋪著瓦片的橋頂,橋里還有賣商品的鋪子。袁庭棟說,有支持馬可·波羅到過成都的學者推斷,這座橋就是當時四川的廊橋樣式。附近城鎮的居民能織出美麗的絲織品。
而在建都、哈喇章省兩地,當地有不少鹽井。當地居民取鹽水煮鹽,制成鹽餅,而且在這些地方,鹽不僅是居民日常食用的調味品,整塊的鹽餅也可以當作流通的貨幣。鹽幣在西藏也是流通的。建都和哈喇章交界處的河流則出產金沙。袁庭棟告訴記者,整個安寧河谷都產鹽,還有鹽源等以鹽為名的縣;金沙江更因富含沙金而得名,這也與之相符。
這一片土地上還有一些與別處迥異的婚俗,匝兒丹丹省的人用金片裝飾牙齒,男人們還要在身上刺青。而路過西藏的商人需要燃爆青竹,嚇唬周圍的野獸,保證自己的安全。
馬可·波羅還提到,貝殼在這些地區也有不一般的地位:既是貨幣,也是裝飾品。而且這些貝殼都是從印度傳來的海貝。如果說他的這段記憶可靠的話,足以說明,那時南絲路沿線的民間貿易依舊活躍。
(責任編輯 :王璐瑤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