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興教寺修復(fù)之后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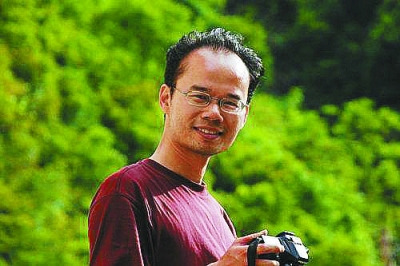
黃印武
□人走了,人來了,人又走了——黃印武在沙溪看到過3次村民的遷徙。在這個“茶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”,他一待就是12年。
□隨著古鎮(zhèn)的修復(fù),他預(yù)想中讓本地人過上更好生活的目標似乎并沒有實現(xiàn)。人們選擇把房子租給外地人,自己搬到更遠的地方蓋新房。現(xiàn)在的寺登村已經(jīng)離黃印武最初的理想越來越遠了。
□很多人擔(dān)心它未來的命運:它會不會成為下一個麗江,或者一片旅游文化商業(yè)的熱土?
人走了,人來了,人又走了——黃印武在沙溪看到過3次村民的遷徙。
2003年,帶著國外的資金和年輕人的固執(zhí),建筑師黃印武最初來到云南省大理州劍川縣沙溪鎮(zhèn)寺登村。在這個“茶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”,他一待就是12年。
起初,他是一名尊重歷史的古建筑修復(fù)者,后來,他做的事情離建筑越來越遠,更像一名鄉(xiāng)村建設(shè)者。
古建修復(fù)的成功猶如打開了一幅邊陲秘境的寂靜畫卷,暴富的客棧老板、酒吧愛好者、咖啡館投資商,欲望膨脹的本地人、野心勃勃的管理者,各色人等陸續(xù)亮相。
當寺登村的發(fā)展脫離了服務(wù)當?shù)厝说能壍溃S印武開始思考行之有效的鄉(xiāng)村建設(shè)道路。那既不是對城市的拙劣模仿,也并非對鄉(xiāng)愁的浪漫想象。
“沙溪不是擺在博物館里展覽的器物,它的建筑、它的街道、它的一草一木、它托舉的日常生活以及發(fā)生在其上的故事,這些‘活的東西’全都是保護的對象”
沙溪給黃印武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人煙稀少。當這個戴著眼鏡、頭發(fā)稀疏,散發(fā)著學(xué)者氣息的建筑師來到沙溪時,一切都像門口貼著的對聯(lián)一樣在褪色——木制的門窗看上去搖搖欲墜,房前屋后堆著破磚爛瓦,村里的人已經(jīng)開始外遷。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駐華代表處文化遺產(chǎn)專員杜曉帆也曾在那時來過沙溪,看了這幅景象,嘴里一直重復(fù)著“怎么辦,怎么辦”。
沙溪北靠藏區(qū),南面是普洱茶的產(chǎn)地,茶馬古道因此經(jīng)過沙溪。這里曾經(jīng)商賈游客云集,三教九流匯聚。自此,小鎮(zhèn)的命運系在交通工具迭代的歷史中。
自上世紀50年代,汽車的脈搏切分著鎮(zhèn)子的時間與日常。馬幫不再榮耀,茶馬古道逐漸衰落,沙溪又重新回歸了寧靜,“躲”在群山中,一待就是50年。
當載著黃印武的吉普車第一次開進沙溪時,黃印武回憶,“感覺像是穿越了”。
那時,黃印武剛剛從瑞士聯(lián)邦理工大學(xué)學(xué)成歸來,在這里主導(dǎo)設(shè)計和實施工作。瑞方希望在茶馬古道上復(fù)制自己成功的古建修復(fù)模式,于是選中了沙溪,有了“沙溪村落復(fù)興工程”項目。整個項目由瑞士聯(lián)邦理工大學(xué)主持,世界紀念建筑基金會籌措慈善資金,“試圖通過對當?shù)卮迓湮幕z產(chǎn)、生態(tài)景觀的保護,實現(xiàn)對當?shù)卮迓浣?jīng)濟的脫貧和文化傳承”。
那時,除了黃印武代表的瑞方,似乎沒有人確切地明白“沙溪村落復(fù)興工程”真正的涵義。在黃印武看來,沙溪復(fù)興中的古建保護,并非單純的建筑修復(fù),而是文化自信心的重建。當村民的信心恢復(fù)以后,村子的發(fā)展才會有自主性,而非盲目追隨別人的道路。黃印武以為,等村子修復(fù)了,人,遲早會回來。
在黃印武剛到縣城劍川,還沒來得及下到鎮(zhèn)里時,縣里的領(lǐng)導(dǎo)就拍著胸脯說:“你們想要什么樣的建筑,把想法拿出來,我們的工匠都能做到。”
彼時的黃印武帶著書生氣,是個靠譜的執(zhí)行者,接到瑞方的電話,總是回答yes,yes,yes,以至于施工隊的工人開玩笑說,打英語電話其實很簡單,只要回答yes就可以了。但他對縣政府的說法還是充滿了警惕:“他們以為這是個‘體力活’。”只要修出來跟以前“一模一樣”的建筑就行了,管它是新還是舊。
在黃印武看來,“沙溪不是擺在博物館里展覽的器物,它的建筑、它的街道、它的一草一木、它托舉的日常生活以及發(fā)生在其上的故事,這些‘活的東西’全都是保護的對象”。所以那些拆了舊建筑,號稱造出一件“一模一樣”的新建筑的做法,在他看來十分簡單粗暴。怎么可能一模一樣呢?老建筑上的一個“疤”,背后可能上演過一段傳奇往事;每一塊木頭都能成為后人工具研究的證物——比如這是用斧頭鑿的,因為那時還沒有刨子。
當時的項目組不足十人,由瑞方和縣里抽調(diào)來的工作人員組成。最忙碌時,要統(tǒng)籌200人施工。楊愛華來到項目組時剛剛20歲出頭,她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在施工隊后面,記錄下他們拆下哪塊瓦、哪塊磚,給它們編號,再重新放回原處。